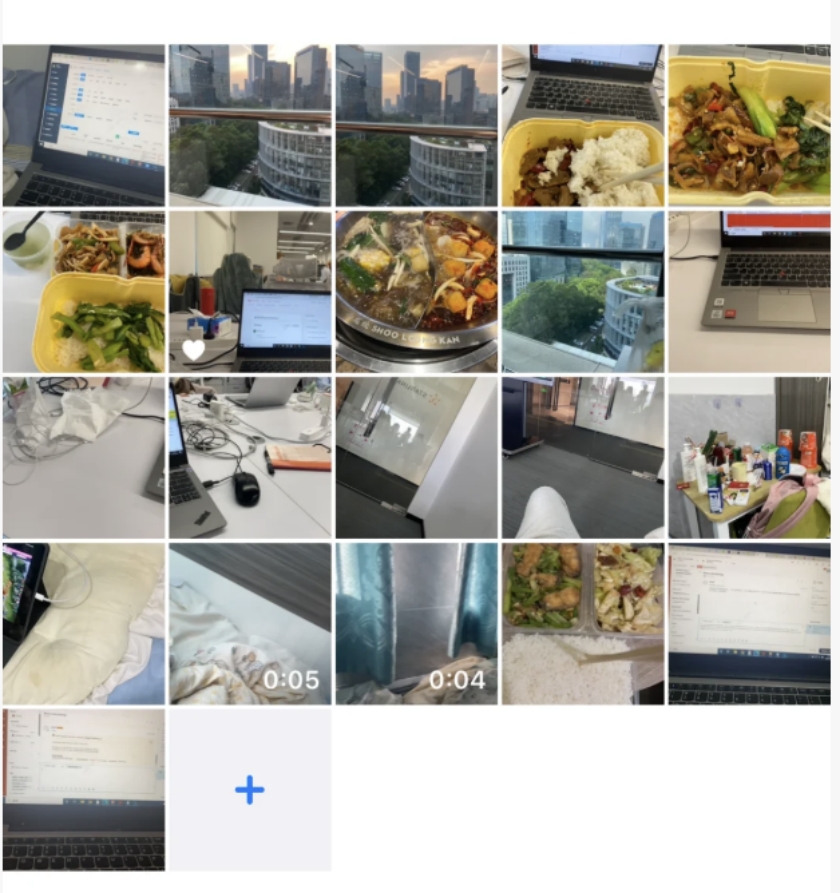靠打工度假签,有的年轻人去澳洲当蓝领|故事
来源网站:telegra.ph
作者:
主题分类:劳动者处境
内容类型: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
关键词:蓝领, 高强度体力, 找工作, 新西兰, 澳大利亚, 生活, 澳洲, 父母
涉及行业:建筑业
涉及职业:蓝领受雇者
地点: 吉林省
相关议题:工资报酬, 人口移动/流动, 海外中国工人, 工作时间
- 王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装修工地上工作,体验了辛苦的体力劳动,但获得了相对满意的工资水平。
- 在澳大利亚,王喆见证了一名19岁工人因为拥有一年的工作经验和较大的体力,在时薪上能达到较高水平。
- WHV签证使得中国年轻人有机会以较低成本体验海外生活,但大多数人在当地从事体力劳动,面临薪酬较低的问题。
- 王喆在国内的工厂工作经历,加深了他出国打工度假的愿望,希望通过改变环境来寻找更好的生活机会。
- 在澳大利亚工作的中国籍劳工常因为签证类型而面临被压价的情况,工作时间长于当地白人同事,反映了劳工权益的不平等问题。
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,仅供参考,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。
靠打工度假签,有的年轻人去澳洲当蓝领|故事财新
【财新网】“有时候真希望我在国内没有读书,而是学门技术,也不至于在这边举步维艰。”23岁的王喆,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个装修工地上工作1个月了。他每天抹墙、刷漆,很辛苦,但工资水平还不错。这是目前为止他在这里找到的最满意的工作。之前,他分别在寿司店、炸串店、麻辣烫店的后厨打工,拿着最低时薪,时常因为出小差错被训斥,还被克扣过工资。
王喆在这个装修工地上见过一名19岁的工人,对方已经有一年工作经验,力气很大,干活又利落,时薪能达到38—40澳币(约合人民币173—182元),特别羡慕。他宁愿自己学的是美发,来到国外就能靠这门手艺赚钱,还容易获得雇主担保。
2023年,王喆从吉林长春一所本科院校的经济学专业毕业。接连经历考公失败、找工作遇挫之后,他进厂打工了一段时间,又把目光投向海外,希望通过WHV签证进入澳洲,做蓝领,攒攒钱。
WHV是Working Holiday Visa(或Work and Holiday Visa)的简称,即打工度假签证,以“赚钱旅游两不误”的特点吸引着全球年轻人。新西兰自2008年向中国大陆开放WHV,每年1000个名额。2015年,澳大利亚通过《中澳自由贸易协定》首次向中国大陆开放WHV,每年提供5000个名额,成为继新西兰后第二个对中国大陆开放此类签证的国家。该计划旨在“增加对旅游服务的需求,并支持澳大利亚旅游业的发展,特别是澳大利亚农村地区”。申请人要求年满18周岁但未满31周岁,只需证明自己有大专以上学历、一定的英语能力和2万—5万元人民币备用金,就可以持此签证进入澳大利亚,合法打工挣钱。WHV签证有效期为一年,可以续签两次;如果想要二、三签,则需申请偏远地区工作以集签。
新冠疫情期间,澳大利亚对华WHV签证申请一度关闭,直到2022—23财政年度重新开放,名额增加了三成,但将签证审批顺序从原先的先到先得改为随机抽签。早期,该签证以“线下抢号”闻名,申请人需在签证中心排队递交材料,场面火爆。改为抽签制后,竞争更趋激烈——2024年10月1日,签证开放申请的首日,中国区报名通道由于流量过大一度陷入瘫痪状态。
持WHV进入澳洲的中国年轻人,大多在当地从事体力劳动,薪酬较低。但在国内求职竞争白热化的今天,通过WHV去澳大利亚、新西兰,被视为普通人低成本体验海外生活、暂时躲避国内职场的“人生旷野”,或年轻人“改命”的机会。
出发的理由
我们采访了一些选择WHV的年轻人,他们都有出走的决心,和必须要出去的理由——有人是为了赚钱,有人是趁年轻看世界,也有人觉得自己“别无他选”。
王喆就属于最后一种。大学毕业后,他陷入迷茫之中,想尽快给自己找一条出路,却无奈于自己文科生的身份——用他的话说就是,没有一份“求生”技能傍身。
他应聘过一家转型期国企的工作,负责拓展市场。试用期有整整半年,到手工资减掉房租和饭钱后,所剩无几。他也参加过国考、“三支一扶”计划,但都没能“上岸”。父母让他去入伍,他为此还花2万块做了近视手术,却在最后关头打起了退堂鼓。
王喆唯一不考虑的就是考研。一次面试经历让他意识到,学历真的在贬值。在一次银行客服岗位的群面中,8个人里,有6个研究生,其中还有专业不对口的工科硕士。“再读两年研究生,就是逃避就业。”王喆觉得,尽管提升学历是大趋势,但他已经亲身体会到就业的艰难,“必须走在共识之前,否则是很难生活的。如果只是随大流,我只会陷入无休止的内卷。”
他把目光投向海外,申请了澳大利亚WHV,但一直没有等到中签。他转换思路,准备申请语言班,获得学生签证入境后,打工赚钱——算上找中介、体检、机票、保险等费用,启动资金不到四万元,这是王喆能想到的“极限低成本入澳”方式。
在出国前等下签的空档期,王喆想真正体验“脱下长衫”、进厂打工的生活。他去了苏州,前后辗转三个工厂——前两个分别是耳机厂和电子屏幕厂,第三个是一家半导体工厂。三个多月的流水线经历,让他出国打工度假的愿望达到顶峰。
王喆在澳大利亚工作过的后厨。图:受访者提供
“00后”湖北女孩Aria出走新西兰的原因,是想看看更大的世界,感受“真正的自由”。
Aria一直都是父母眼里的乖乖女,从上幼儿园到大学毕业,不曾越出父母划定的“安全区”,甚至不曾离开湖北。大学时,Aria就读于省内一所高校的商务英语专业。她毕业后的生活不算太顺利——考教资,两次在面试上失败;专八没有通过;在武汉找了一份新媒体运营工作,薪资很低,只干了半年就辞了职。
Aria从小就梦想去国外看看,曾经试探地跟父母提出,想在国外打工度假一年。父母反应激烈,希望她能留在省内考研、考编,甚至以断绝关系相逼。Aria只好答应,但提出先去别的城市上班,攒点钱,再回家。双方都做了让步,父母妥协了。
一直到今天,Aria的父母都不知道,女儿其实不在深圳的格子间里做白领,而是在新西兰一家超市里切寿司。
为这场“出逃”,Aria预谋并准备了整整405天。
她的确在深圳一家外贸公司找到了电商客服的工作,上了十个月的班。但这是为了去新西兰的一步棋——当时,她一边上班,一边为申请新西兰WHV做准备。“我想了很多个办法,我当时人和他们住在一起,该怎么出国呢?最后我想到了,如果我远离他们,去外地打工一段时间再出国,他们不就发现不了了吗?” Aria说。
与如今澳大利亚WHV实行抽签制不同,新西兰实行的是抢号制——澳大利亚WHV申请全凭运气,新西兰WHV则更依赖网速和手速,先到先得。其“手慢无”的抢号模式也催生了中介代抢服务费,有的高达万元。
为了稳当,Aria花了1.5万元找了两家中介,一下子花出去了三个月的工资。最终,其中一家成功抽到了签。拿到WHV签证让她有了盼头。她每天倒计时,立下了出发前的目标,有攒钱,有减肥,有练习口语,也有找到同行的搭子,规划得井井有条。尽管每天上班时都要回复一两百封邮件,常常头昏眼花,“但是一想到离新西兰越来越近,我就非常开心。”她甚至专门创建了一个相册,拍了许多报备照片,以应付出国后父母的询问。
为了假装自己还在国内,Aria在深圳上班时拍了很多照片。图:受访者提供
临近签证提交截止的最后期限,Aria存到了5万元。卡着最后几天,她从深圳出发,到北京转机至新西兰。出发的第二天,正好是Aria的生日。
“抵达新西兰的那一刻,我是真的感受到了自由,是一种不再被父母束缚的自由。”Aria写道。
对另一些人来说,出走澳洲是为了从忙碌生活中抽离,花些时间来认识自己。
小季去年毕业于一所“211”院校的新闻学专业。原本一心想扎进影视行业的她,在实习中受挫——看到自己和其他实习生就像光鲜行业背后默默无闻的燃料,“有点理想破灭的感觉。”
本科期间,她去过三家电视台、两个电影节;短视频、广告、ESG行业,她一一实习过来。简历塞得满当,小季却越来越迷茫,“干一行恨一行”。
大四时,她拿到上海一家“4A”广告公司预转正实习,实习时长四五个月。跟过几个项目后,她慢慢发现,带教姐姐的生活状态也许并不是她期待的未来——工作强度大、节奏快,小季不想在这里花上四五年时间。对工作压缩精神世界的恐惧,让她又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岔路口。
她突然意识到,在看似繁忙充实的大学四年里,自己好像从来没有问过内心真实的喜好。她想,离开按部就班的轨道,其实还有很多可能性:换个专业,换个环境,换种体验,完全可行。
在父母的“放养”下,从高中升学到大学报考,小季习惯了自己做决定,这次出国的决定也是自己做的。经过一个星期协商后,父母同意她放弃实习公司的转正机会。
去年,小季独自完成了澳大利亚WHV申请;11月签证下发后,她买了今年3月前往悉尼的机票。南半球这时正在缓缓入冬,她提前找好了雪山脚下一家餐馆厨房的工作。曾在咖啡馆兼职过的她,对接下来的工作充满期待。
小季偶尔也会感到有些可惜:那些工作和大学专业毫不相关,好像浪费了自己拼命实习的经验。但她明白,过去那种马不停蹄工作,但很少倾听自己内心的生活,需要暂停。她要用一段时间的空档期,慢慢了解自己,再在一个领域深耕下去。
站在“人生旷野”上
2025年春节前,王喆在墨尔本找到了这份装修工地的工作。回忆起在国内流水线的经历,王喆感觉,自己从一种廉价劳动力,变成了另一种廉价劳动力——工地上的许多中国籍同事都是依靠学签来澳打工,因此会被压价,“收入全靠工时堆”。同是早上七点上班,白人同事下午三点就下班了,中国籍同事会工作到下午五点左右。而且,工资差距很大。尽管如此,他很满意这份工作,打算做工熟练了就去谈涨薪,“有盼头。”在他工作过的几家餐厅,除非做到店长或主管,不然只能一直拿最低时薪。
上班时,王喆会戴着耳机,听播客、听书。他也很喜欢同事间热情友好的氛围。起初,他只能做一些边缘的收尾工作。白人同事路过,也会拍拍他肩膀,竖起大拇指说:Good job(做得好)!他也发现,工地上的外国人会穿着工作服坐地铁,从不担心被打量或别人有异样眼光。
生活渐渐稳定下来,更大的敌人变成了孤独。澳大利亚和中国有时差,王喆和国内的朋友慢慢生疏了。每天结束了高强度体力活之后,他几乎没有多余的力气出门,也不愿意牺牲休息时间去社交。
王喆在装修工地工作。图:受访者提供
Aira同样感受到了身在异国他乡的孤独。
由于新冠疫情期间新西兰的“移民大赦”政策,岛内体力劳动市场愈发饱和,找工作变得很难。一些通过WHV来到新西兰的年轻人,甚至在“倒贴钱打工”。有人称,“如果说WHV是‘旷野’,那么这片旷野上也站满了打工人”。
不过,Aria并没有在找工作上卡太久。圣诞季来临前,一位当地的华人姐姐就联系上Aria,为她在新西兰皇后镇周边一家超市的熟食区找到了工作,还把家里的一个房间提供给Aria租住。
尽管其23.75新西兰元(约合人民币98.96元)的时薪刚刚超过新西兰规定的最低标准,她仍然在这里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鲜。和在深圳时一样,她现在每天工作8小时,不同的是,在这里每隔两小时会有一刻钟的休息。在扣掉高达17%的税款后,她拿到手的工资仍然是国内的两倍还多。
为了省钱,Aria没有买车。有段时间,她每天凌晨4:20起床,走路17分钟,到岗,换上工服。她要面对的不再是源源不断的邮件,而是一波波寿司和烤鸡。——每天要么煮饭,切鸡肉,做鸡肉饭,洗寿司机器,洗盘子,准备第二天的米饭和鸡肉;要么烤鸡、做三明治、热食、切三文鱼——在简单而重复的工作里,一天很快就过去了。她发现,切好一片厚薄适中的牛油果,并不比发好一封英文邮件容易。
Aria的超市工服。图:受访者提供
工作的第一个月,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。Aria的交际圈只有华人姐姐一家和两个同事。因为时差的关系,国内朋友的消息她也不能及时回复。父母打来视频电话,她总要提前跑到图书馆才敢接通,假装自己正在备考。
不同于王喆,对张逸然来说,WHV并不是“别无选择”。他本科时在马来西亚读法语专业,实习时做过一段时间数字游民,毕业后顺利拿到法国一所高校的研究生offer(录取通知书)。巧合的是,WHV也在同一天下了签。经过一番思想挣扎,他决定选择WHV。因为WHV只能在30岁及之前申请,一生只有一次机会,但他可以随时选择去深造。
但就像王喆想要“劝退”国内白领那样,张逸然也同样劝退过自己的朋友。
张逸然落地墨尔本时,恰好是圣诞季,当地正在放长达一个月的假期,找工作很难,三天面试五场,但都不顺利。最后只能接受极低工资,一边做销售,一边骑驴找马。有时,他还会接到骚扰电话,让他选择英文还是中文服务,“你选英文,就会挂断;你选中文,就会来骗你。”
那几天,他住在16人男女混宿的青旅里过渡,花着人民币在澳洲生活,快要把存款烧光,让他非常焦虑。他用“恐怖”形容那几天的状况,“天塌了”。
此后,在澳大利亚的8个月,张逸然在木屑飞扬的木料厂里当过学徒,去酒吧和赌场做过服务员,也去矿区端过盘子。一开始,体重只有110斤的他,连工厂里的木头都搬不动,受伤、留疤是常态;吃饭也很糊弄,每天只能啃着干巴面包。
他把这些情况发给朋友,说:“在国内还能混下去的话,就别来受这个苦了。”
不过,尽管体力活很辛苦,张逸然非常喜欢打工度假的生活。在澳大利亚,他像是短暂走进没有peer pressure(同辈压力)的真空。矿区的许多同事会一边上班,一边学习和健身,“卷自己的身体素质和能力,而不是坐在工位上,卷无意义的工作时长。”这种劳累,是他愿意接受的。
他也收获到许多“比钱更重要的东西”。他观察到,在一个充满多样性的环境里,每个人都在被包容,也因此会包容他人,无论宗教信仰、性取向、做蓝领还是白领工作,“我自己做过体力劳动,还是个酒鬼,我受到了接纳,所以包容和接纳他人也是我的责任。”
打工度假的底色是快乐的,但也常伴着酸涩的滋味。“无数细碎的小事都在提醒着我,我只是背包客而已。”张逸然说。
在昆州(昆士兰州,Queensland)一个非常小的城市打工换宿时,张逸然遇到了好客的一家人,还有三只听话的小狗。他会和房东一起遛狗,也交到了不少好朋友。他太想留下了。可是为了续签,他必须申请各种偏远地区工作集签,不停地换工作、换城市,不能在一个地方久留。
打工度假之后
国内社交媒体上,有人称打工度假一年还完助学贷款,还赚到了留学学费,也有人称自己打工度假两年攒下50万元。
不过,也有一些年轻人在澳洲亲身体验打工度假后,不得不去除滤镜、面对现实。比如,张逸然发现——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能赚钱,“本来想猛干几年,一年起码攒15万元,最后发现不是这么回事。想要(靠WHV)翻身,也不是没有可能,只是必须好好规划,非常能吃苦。”
今年春节除夕那天,Aria难得有了一天假期,她走去家附近的餐馆,点了一份泰式炒饭犒劳自己,当作年夜饭。平时,她舍不得下馆子。窗外是和国内完全相反的季节。“我怎么这么惨?大年三十,一个人在外面。”Aria看着父母发来老家的照片,想着再坚持几个月就回家。
勇敢,是Aria对自己的24岁的注解。她的目标是存够15万元,而4个月的时间,她已经完成了一多半。8个月后,Aria打算回湖北考公。她明白,自己已经体验过梦想的生活,学会了更多生活技能,最重要的是她认识了世界。
集签失败后,张逸然不得不离开澳洲。像原本规划的那样,他继续申请了法国的研究生,不同的是,比起一年前,他攒下了钱,后来还以游客身份回到澳洲玩了一段时间。
现在,张逸然身在法国,打工度假仿佛已经过去很久,但腿上的旧伤还会隐隐作痛,也成了那段美好日子的提醒。有时,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脑力劳动,他会很想念干体力活的日子,在出汗中分泌多巴胺,放空大脑,快速赚钱。所以,他一边读语言班,一边继续在当地餐厅打工。
来澳洲的这几个月,王喆已经把语言班学费赚回来了。不久前,WHV签证也下签了,他打算从语言学校退学,依靠WHV签证留在澳洲。
“健康是第一要义。”王喆知道,工地的高薪是牺牲健康换来的——工地上的粉尘和噪音,积年累月的高强度体力活,都可能造成职业病。
他的目标,是疯狂打工三年,攒够一百万元,去东南亚国家“躺平”。王喆去过越南、泰国、老挝旅游,也研究了定额存款的利率,希望利用汇率差,依靠被动收入,节俭地生活——实现“FIRE”梦想(“Financial Independence,Retire Early”的缩写,即“财务独立,提早退休”)。
王喆觉得,但凡在国内职场还有不错的选择,就不必放弃原有的生活,申请WHV“没苦硬吃”。在他看来,许多WHV中介过度渲染打工度假生活,只提赚钱多,却对高昂生活成本和高强度体力活闭口不提。今天的WHV不仅意味着高强度体力活、全英文的交流环境,也意味着越来越激烈的求职竞争。通过WHV“逆天改命”,终究是属于少数人的神话。